談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文/龍應台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
H. G. Wells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台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裡拿著書──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
查:你為什麼害怕呢?──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欲會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雙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這你明白嗎?
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檯燈。存在主義彷彿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
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鍛造冶煉自己之外,也沒有別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這些,否則人不能做什麼。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沙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於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裡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裡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餽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零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思想的紀律,絕不是去束縛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發展思想。中國知識界現在就正缺少這種思想上的鍛鍊。
漫天砲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朗誦又難記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零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零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裡,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梁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樑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裡,教育的目的──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裡所揭示的:
[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憲法不是從別人那兒抄來的,反倒我們是別人模仿的典範。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凌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於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裡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 Wells在「歷史大綱」(1920)裡寫了這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岐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我青年時期讀到的沙特。然而這並不奇怪。沙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包 (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時代」裡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於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台海兩岸的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沙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
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裡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裡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九國和第十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闊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定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里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里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飢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溶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我們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幹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所以,今天的大學生,面對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需要什麼「基本配備」?
顯然這個問題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台上。百分之六十的封面是一個或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兩首交叉在胸前,帶著極度自信的微笑,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百分之四十的書籍或雜誌會把「競爭」或「實力」寫在封面,警告你早做準備,全力衝刺。整個賣書區,瀰漫著一種全球化「來襲」,害怕掉了隊的恐懼,或者說,恐嚇。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裡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資訊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的暗面──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卻不見蹤影。為何「指南」書籍和雜誌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或者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全球化的真正議題,哪裡只在競爭呢?如果你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沈的船上,去搶電影院裡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裡,缺乏宏觀與深沈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不是只有跨國企業增進經濟利潤這一件事,它更包含了種種文化價值衝突、貧富不均和環境掠奪的問題。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議題是人類社會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裡,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裡競爭得利,掙錢搶先?
思考全球村的未來的責任,難道不在「公民」身上?如果在羅家倫時代,大學生被要求以道德、知識和行動參與來對他的「國家有難」負起責任,我們今天對大學生的期許,顯然就不能侷限於「國家」而必須以「全球村」為單位來思考,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今天問題的解決也不再是單一國家的解決。以單一國家為範圍的公民意識勢必要轉型成另一種東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識」。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
• 兒童權益國際財政
• 沙漠化自然災害
• 教育 和平促進
• 環境 脫離貧窮
• 食物安全國際難民
• 性別平權稻米與農業政策
• 農村發展都市化問題
• 全球健康志工
• 愛滋病 水資源
• 人權 政府管治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
2. 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
3. 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貧窮地區的人民。
4. 受沙漠化危害最大的是非洲,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可耕地,而且在持續惡化中。
5. 百分之二十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
6. 沙漠化帶給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工,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字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愛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
自從一種抗愛滋的新藥(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愛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藥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金,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製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藥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藥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作法卻違背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藥的智慧財產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藥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衝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對於貧窮問題,學生所學的基本常識是,全球有七億人食物不足。每年有一千兩百萬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或飢餓而死亡。但同時,全球其實有足夠的糧食生產,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三千五百卡的熱量分配。所以人間有飢饉,並不因為糧食不足,而因為糧食的運輸和分配有致命的問題。
國際樂施會的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字是這樣的:
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裡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裡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全球公民教育的特點是,它不止於知識層面而強調參與和行動。譬如咖啡的生產和供銷過程中有非常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因此樂施會固然對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提出要求:
──協助咖啡農生產多元化,減低對咖啡的依賴性
──發達國家減低關稅和貿易壁壘,增加農民的選擇;資助農村發展,給予農民在資金與技術的支援,逐步發展其他生產
同時對咖啡貿易商施加壓力,要求歐美貿易商:
──以一個合理的價格(高於成本,並可支付基本生活開支)向農民訂購咖啡豆
──應與農民訂下長期合約,以免農民受短期價格不穩而無法維持農田的生產水準
──協助農民改善農產品質素,加強咖啡生產的可持續性
更直接要求全球公民採取行動:
──購買公平貿易貨品
──要求零售商提供公平貿易貨品,以供選擇
──參與消費者運動,向企業提出全球公民的關注點和要求
這些先進國家在進行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本土「愛國教育」,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課程都不是為大學生設計的;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和初中生。全球公民教育,不始於大學而始於小學。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國際樂施會對「全球公民意識」下這樣的定義:
全球公民意識不僅只是自覺我們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強調我們對彼此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深切認識到人類需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
全球公民意識指的是我們體會到地球的不可替代並且以行動去保障它永續的未來。
全球公民意識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一種人生觀,一種信仰──堅信行動可以帶來實質改變。
我們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
──他的關照面超過他的本土而且自覺是全球一員。
──他尊重多元的價值。
──他對全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和環境的關連與運作有所瞭解。
──他對不公不義的事會感到憤怒。
──他會參與,不論是當地的或國際的事務。
──他願意以實際行動來為地球的永續努力,他對人類社區的未來有責任感。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鴻堡分校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唸一段誓詞:「在選擇工作或服務機構時,我務必考慮該項工作及所服務機搆是否承擔對社會及環境的責任。」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擬出另一個版本的大學生誓詞:
我承諾將致力於建設一個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應用必須以社會責任為念。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量。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做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拼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唯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如果台灣的大學生也有這樣的認識,他可以怎樣地自我要求呢?
第一,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釐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台灣在民主開放之後,對社會最大的挑暫毋寧就是人民思辨的能力。在黑與白之間,出現眾多層次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更凸顯一個事實:沒有思辨能力的民主,只能往一個方向走,就是沈淪。
第二,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反比台灣的狀況,不免驚駭。三十五年的國際孤立,台灣人被排除在全球社區之外,集體自覺邊緣,全球意識難以建立。政府決策者以鎖國心態治國,媒體業者以一種病態的內視媚俗,都和三十五年的國際孤兒處境有關。在火熱的、短線的政治權力鬥毆裡,真正重大、攸關未來的議題很容易被認為空泛、遙遠、不切實際。
可是,我不認為列強在中亞儲油資源豐富地區的縱橫捭闔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伊朗的核武發展與台灣的安全無關;我不認為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人權的態度與台灣的未來無關;我不認為北極的冰山暖化與台灣的生存無關;我不認為全球水資源的匱乏與台灣無關;我不認為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台灣的處境無關;我不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地位。。。
我不認為台灣可以在孤立的心態中繼續存活。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心態封閉的社會裡,台灣的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部長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無能而混亂的政府,越過低智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第三,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裡,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台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台灣人遠遠走在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先鋒。只不過關懷的範圍大多侷限於島內議題,很少對於全球的探討。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第四,品格的培養。 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
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裡,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擅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毛澤東嗎?今天的台灣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也有痛楚的體會: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裡沒有一個指導的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思辨能力、知識、行動力等等,都是闖蕩開拓的動力,但是沒有一條船可以沒有錨。品格,就是錨。沒有錨的船將隨風勢飄盪不知所終,沒有品格的人才也會使社會暗夜盲行,邁向觸礁沈淪。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鍊、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沙特所說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沙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物換星移,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仍舊是最關鍵的問題,只是範圍提升至全球,而且更為迫切。
今天掌權的都是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趁著全球化的新知洶湧,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零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值得參考網站及書籍:
http://www.gapminder.org
http://www.citizenship.global.org.uk
http://www.globaleduc.org
http://www.oxfam.org
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
http://www.iyfnet.org
http://www.youthactionnet.org/quizzes/global_citizenship.cfm
http://www.globalissues.org
Smith, David J. If the World Were a Village: A Book About the World’s People. New York, Kids Can Press, 2002
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龍應台】災難和教育的拔河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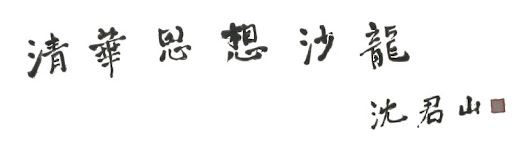
 思想夥伴們:
思想夥伴們:
0 意見:
張貼留言